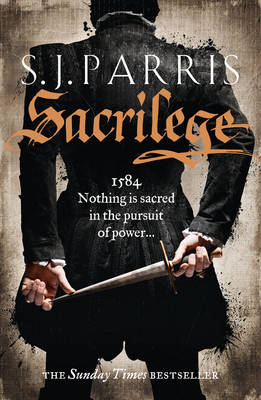导游书上说,布拉格出租车不靠谱,只有AAA和111两家可以信任;会议手册上也有警示:宁可电话叫车,不可随手打车。MMP这本小说里也提到,她和加拿大朋友打车,最后收费160kc(约6胖子),加拿大人惊呼便宜,而作者因深谙布拉格出租车的把戏,则惊叹自己上车是没留神,被计价器狠狠地宰了一刀。
小巴对这种事情很警觉,出机场之前就嘱咐我说,我俩一定非这两家公司的车不坐。但我总觉得这有点耸人听闻的意思——都什么年代了,国际都市,出租车计价打表,能有什么差错?我总觉得被坑的人一般都是上车马马虎虎没有让司机打表的,到了目的地多少钱自然只能听司机摆布。
好在反正机场外排队等客的都是AAA和111,完美规避了我俩过度紧张与过度潇洒的矛盾,我俩顺利坐上一辆111,开赴城里。一路只见各色斯柯达汽车飞驰而过——果然是到了捷克了,满眼都是这流动的地标。
我感觉布拉格似乎不大,因为只用了30分钟,出租车就把我们送到了市中心旅游区边上的酒店。收费:450kc。比旅游书上估价的600kc还便宜。我马上跟小巴说:你看,完全没有书上说得那么夸张吧!
小巴点头说是,马上也放松了警惕。随后的几天打车,小巴基本上是计较表显示多少就给多少,也没过脑子。我却惊讶的发现:我们在城里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同样打表坐AAA和111的计程车回旅店三次,均大约5-6分钟的车程,三次车费分别是:300kc,160kc和250kc!!直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真正”的价码应该是多少钱。虽然相比英国车费依然很便宜吧,但我算是领教了,布拉格出租车果然很坑爹。
这是后话,话说出租车送我们到了酒店,check-in,进房间拉开窗帘往外一看——

囧。哎,3月份不都应该是春天了么。问当地人,布拉格往年也是如此么?当地人都把头要得如拨浪鼓,说哪里有3月份还穿羽绒服的,今年头一遭。
不过我和小巴不怕,去年年底在北京俺俩已经接受过零下五度的抗冻训练了,区区零下一度算啥?俺俩放下行李就出发去会场了,短暂晃悠了一下之后,饿意袭来,转身决定去老城了,而且毫不见外地选择了坐地铁!

说起来布拉格的地铁车票真好看,防伪工作我觉得比英胖子都复杂——
24kc(不到1胖子)可以坐30分钟的公共交通,相当于贯穿整个市中心了。便宜哇!让我又忍不住要吐槽一下英国那又贵又不給力的公交,可忽然想起来飞机上看得(2010年的)旅游书上说这个地铁票应该是17-18kc,也就是说过去3年,布拉格的公共交通涨了33%!但总体来讲布拉格人民还是挺幸福的,地铁干净又方便。
出了地铁站,我俩本来攒足了赞叹准备被震撼的,但面对眼花缭乱的屋顶,我俩都有点懵,两个对建筑都一窍不通的家伙理不出个头绪来。
但有个事情我是可以理出头绪的:吃!
出地铁没走几步就看见这么个小吃摊,“trdelnik”,传统斯洛伐克小吃,我和小巴管它叫“turtleneck”,反正面团绕在木棍上样子和turtleneck也差不多,炭火一烤,外面再裹一层糖粉和果仁~Mmmm~

刚吃完turtleneck,转过街角就看见下面这个神秘女子——

知道这是在烤啥?土豆。
果然是土豆大国,烤个土豆都不同凡响,你看可是同是烤土豆,和英国夯实的jacket potato比起来,不觉得这种烤法更妖娆么?

天气太冷,在室外不能多呆,我俩马上在一条偏巷里找了一家看起来靠谱的酒吧坐下,摊开小说看了没几页,俺感觉外面“忽然阴天”了,一片片阴影遮到书页上,抬头一看窗外就聚集了一群游客往里张望——原来俺俩无意走进的这个酒吧还是个景点,一队队地游客是来张望酒吧里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叫Golem,犹太教的人偶,传说很多,最终因脱离管教而被废弃,但废弃前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帮你打理家务,擦个地板挑个水啊,都是Golem在行的。
大Joy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咦,现在研制家务机器人那么火,以后真研制出来取名Golem多恰当!
哈哈!后来回家一查,嗯,咱的想法也并不离奇,这俩确实有点关系:英文里的“Robot”一词源于捷克科幻小说《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虽然作者Karel Čapek不承认,但是因小说脉络和Golem的传说相似点颇多,Golem多被认为是Robot的鼻祖——你看,我就说布拉格是个特别穿越的城市吧。
回到那个小酒馆里,游客扒在玻璃上向内张望,猛然看见窗下的我和小巴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则很“当地人”地坐在位子上向他们招手致意,哈哈,看我从西欧土豆国飞来东欧土豆国,融入得很快吧!
吃饱喝足,暖和过来,我俩又冲进大冰窟里。我们的目标是在找到卡夫卡出生的那座楼。
按理说地图上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了,就在老广场侧面的一个小空地上,可是我们居然就在这个空地上走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任何“入口”,最后是在两扇貌似艺术展览的大窗户与巨大的卡夫卡咖啡店店门之间,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门,从外面看,说不好是不是在营业。
小巴很绅士的在3米外的距离仔细打量了一下,推理的结论是:好像不开门。
大Joy则是地道的“实证社会学家”:开门与不开门,用脑子推理是没有用的,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亲自用爪子推拽⋯⋯结果俺一推,门还真开了!

一个并没有太多藏品的小屋子,但卡夫卡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哎!还是挺酷的。
后来我们发现原来在布拉格,大Joy的“动手推门”法是最有用的找路的方式,因为不论是教堂、餐馆、博物馆还是商店,开门都开得特“隐晦”,要保留大不了颠的矜持,基本就那里都进不去了。而且也不怎么标哪里连着哪里,或者哪扇门是通向哪里,所以经常的情况是:要么是转了一圈也找不到入口,要么你会发现一个堂堂大教堂的入口掩藏在几层餐馆酒吧的门后==||
第一天的见闻基本如此。晚饭我俩走进一家叫Lippert的百年老店——开始,如同布拉格几乎所有的服务单位,我们搞不清楚里面是不是在营业,直到大Joy“推门而入”,赫然看见——
就这家了!
之后在布拉格呆的4天半里,我们来这里吃了两次,其中美味下下回再叙。